如何构建同理心
翻译:王雪纯 审校:高知寒 | UXRen翻译组 #345译文
作者: Seung Chan Lim
原文标题:《What is Empathy?》
如果我们仔细审视生活和设计中的同理心,就会发现它不仅仅关于接受,也关于给予。
同理心(Empathy)已经成了一个流行语
一般来说,离流行语远点儿总没错。同理心也不例外。
我第一次接触“同理心”这个词是在10多年前。我那会儿刚大学毕业没几年,身边有个好朋友深受躁郁症的折磨,出于想要帮助她的愿望,我去咨询了心理医生。
第一次和心理医生见面时,她建议我试着和朋友共情(empathize )。我问她该怎么做,她让我先学会倾听(Listen)。“倾听?”我问自己。“我当然知道怎么倾听啦!”我心里这样想。
我错了。
我错误的自我感觉“倾听”就是“听着”,就是仔细听别人说话并且不打断。然而,只是听,而没有适当的回复和追问,还远远不够。
让我通过分享我的书《实现共情:探究创造的意义》中的一段摘录来说明这一点。这段摘录描述了我做木工时的一次经历:
阳光透过工作间的落地窗洒进来。我站在工作台上固定好的的长木板前,耳朵里传来咚咚的锤子敲击声,还有叮呤咣啷木板夹晃动的声音。我来来回回的在木头上拉着我的日式锯子,试图挖出一些凹槽来做细致雕刻。
当我正专心的努力用锯子切割出一条直线时,我发现一位木工师傅站在房间另一头,一动不动的盯着我。
“你知道吗……”师傅说,我站直了,等他说下去。“如果你仔细听,木头会告诉你你锯得如何。声音是非常诚实的。”我愣住了,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他这充满禅意的话。“你再试一次。”师傅建议说,“并且这一次,仔细听”
于是我俯身又开始锯,并开始注意锯刃摩擦木头的声音。但我没听出什么特别之处。
“现在……”,教练打断了我,并伸手松开了夹着木头的钳子,把木头放低,然后重新把木头固定起来。这回木板露出工作台还不到两英寸(5厘米)。“再试一次,仔细听”
我再一次把锯子放在木头上,慢慢开始来回拉锯,并很快就形成了稳定的节奏。然后我听到了。
或者我应该说我没听到什么特别的,只是某种沙沙的声音。我猜那应该是沙沙的声音。我现在回想起来,已经记不清那个声音是什么了,只记得像是牙齿咬下苹果时发出的声音。
“哦,哇!我现在听到了。太棒了!“我脱口而出,心中不由敬畏起来。
回想起来,在木工师傅降低木板高度的那一刻,我就应该意识到我做错了什么。我把木板固定得太高了,导致它来回震动,结果让它发出一种类似沉重家具被拖拽过地板的摩擦噪音。
师傅是对的。木头是诚实的。但直到现在,我都没有在倾听。
或者更准确地说,我听到了声音,但我太忙着锯出直线,所以并没有试着去理解这个声音意味着什么。或者更糟的是,我以为我知道,因为我觉得锯东西的声音就是,嗯……锯东西的声音呗。就算声音的确有些区别,我觉得那也没什么意义。事实上,正因为我认为声音不会有什么不同,所以它们才对我没有任何意义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压根没留神听。而不仔细听,我更不会觉察出区别,只能白白浪费了这种真诚的反馈。
我们从“客体”(“Other”)获得的信号,无论是从别人还是一块木头那儿,都会被我们放置在自己最熟悉的认知模式中解读。但自己最熟悉的认知模式却只能提供解释的一种可能。
你有没有十几岁时读过一本书,成年后又读一遍的经历?你有没有惊讶的发现儿时错过的“言外之意”现在如此“显而易见”?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受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你发展出了更全面也更细致的认知模式,从而你能更好的理解书中的内容。我的书里收录了一次采访,布朗大学(Brown University)的儿童心理学先驱之一Lewis Lipsitt博士将上述过程称为成熟(maturation),即经过仔细的审视和思考,在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的事情里发现了与之前的理解不同的含义。
类似的,木匠师傅因为帮我拓展了认知宽度,让我更加成熟。在新的认知模式下,我能够重读之前接收到的信号,并且从中获得不同的体验与理解。如果没有这种新的认知模式,再加上缺乏探究,锯东西的声音对我只是一个抽象的声音符号而已。在下面的TEDx演讲中,我更深入的探讨了这个话题:
https://youtu.be/CGLUzYUKhTs (需翻墙访问Youtube网站)
在这次演讲中,我分享了自己之前是如何对木板、朋友以及同事缺乏同理心而不自知的故事
对同理心的阐述
在主流媒体中,把同理心说成是“读心术”或“感同身受”已经变得很普遍了。虽然这么说也可以理解,但很容易让人把手段混淆为目的。
“Empathy”(同理心)是由德语单词”einfühlung“演化而来。Einfühlung这个词是用来表达人们与艺术作品融为一体(通常被称为”同一性”)的感受。这个词描述了物化的”主体“与”客体“之间边界模糊但却没有完全消失的体验。这种体验通常被喻为是好像”走进“了一件艺术作品,无论是一幅画、一件雕塑、一部小说,还是一场表演。直到今天,当我们说”站在别人鞋子里“时,我们仍在使用这个比喻。
说到共情,有三种不同的状态,这三种状态总是与“客体”有关。”无共情(Not empathizing)“发生在当你无法感受到和”客体“的统一感的时候;”共情(Empathizing)“发生在当你可以体会到统一感时;”错误/过度共情(False or over empathizing)“发生在当你无法区分”主体“和”客体“的时候,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有压力,并且不是很愉悦。
如果说共情是指我们从无法体会与”客体“之间的统一性,到能够体会到的这个过程,读心术(也被称为观点采择(perspective taking)或心智理论(theory of mind)),或感同身受(也被称为情绪感染(emotional contagion))也许的确有其作用,有时甚至很必要。然而,他们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。而目的本身应是统一性的体验。
想象一个球滚下山顶的画面。同理心就像是这个球在山顶时拥有的势能。共情的实现就好比是当球已经到达山脚下的状态。在与”客体“互动过程中(不论“客体”是一个人,一块木板,还是一件艺术品),同理心可以将我们从”无共情“的状态(没有体验到统一感)带到”产生共情“的状态(体验到统一感)。同理心的实现有很多要素,学界目前还没有统一定论。
有时共情的实现是不知不觉的、被动发生的。举个例子,很多人在看电影或小说时,常常能够自然而然的与虚构的人物角色产生共鸣。但共情并不总是如此自然实现。当你觉得面前的人”愚蠢“、”错误“甚至”邪恶“的时候,共情就没有自然而然的发生。
当我们遇到无法与之共情的”客体“时,我们就在谷底。如果希望共情产生,我们就需要从谷底爬上去,我把这个爬升的过程称为”实现共情“(realizing empathy)。伴随这一过程产生的就是成熟。
在阐述实现共情的实践时,我指出了四个互为补充、相互作用的过程,前面提到的”倾听“就是其中之一。
仔细看”实现共情“的过程,实际上有四个互为补充又相互独立的过程共同协作,才能使共情成为可能。
同理心在设计中的作用
在设计界,我们经常将同理心当成获得洞察的工具。我们说要通过采访、观察、角色扮演或要以某种方式从用户那里收集信息以研发更好的产品。这种使用共情的意识让我们的研究方法可以做到以用户需求为中心,的确比那些不在乎用户想法的方法好。然而也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限制,有时甚至可能是不道德的。
- 共情不能仅局限在我们与用户之间,也可以发生在我们与客户、与同事和与我们用来做设计的原材料之间。
其实,它甚至可以发生在我们与“自我”之间。你可能会时不时地对自己说“我今天感觉不像我自己”,或者“我都不太了解我自己”。这些情况可以被认为是我们无法对客体化的“自我”产生共情的迹象。从根本上说,共情可以发生在与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任何客体之间,不论这个客体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。以这个角度来看,我们设计产品和服务的工作就是与不同“客体”之间产生有机联系的过程。换句话说,我们所说的产品和服务就是实现共情的结果。 - 对洞察力更好的定义应为实现共情的副产品,而不应是目标。
只专注于从别人那里获得洞察会把同理心矮化为纯粹的工具。一不小心,这种做法就会对我们与“客体”之间的互动带来负面影响。审问与访谈之间、以操纵/利用为目的的了解和以支持为目的的了解之间,是有区别的。表面来看,这些似乎是截然不同的行为,你一旦深入其中,你就会开始意识到,这些行为之间其实只有动机不同的微妙区别。 - 理解(understanding )只是我们能够和“客体”产生共情的方式之一。
共情的另一种方式就是简单的和他们呆着: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全情感受与他们呆在一起产生的统一感。这个时候,除了对这样的相处会带领我们去向何方保持适当的好奇,保持到足够让我们愿意沉浸其中的好奇程度之外,不需要预定任何目标。当我们想要和同事一起碰撞出新的、意想不到的想法时,当我们想要用物料创造出有突破性的东西时,或者当我们只是想简单和某个人呆在一起什么都不做时,和他们简单呆着就好。 - 一旦你意识到共情不仅局限于用户,并不再把“理解”作为与他人共情的唯一方式时,你就会开始注意到,共情不仅仅是接受,也是给予的过程。
有些人倾向认为共情的过程不需要付出。这种想法可能在有些情况下是成立的,但本质上却是错误的。当回顾我在研究同理心时探索的各个艺术领域(即表演、舞蹈、绘画、雕塑、木工等…)时,这一点变得非常清楚。比如,表演中的共情同时体现在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对角色的表达中。技巧层面上来说,如果演员不能在表演时做到像理解角色时那样全情投入,观众就无法理解演员想表达什么。进一步说,如果演员不能完全沉浸在表演中,观众会本能的觉得不对劲,会给人留下“假的”或“俗套”的印象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我们作为设计师所做的事情。 - 我在研究共情过程中发现的最美好的一件事:当我们能够与“客体”实现共情,我们实际上也就更能理解“主体”。
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:当你试图将什么事情给别人表达清楚时,这个过程其实也加深了对自己思考过程的理解?或者是,当你试图教别人一些东西时,其实也增进了自己对内容的理解?只要动机是诚挚的,实现共情本质上是互惠互利的过程。这种互惠互利指的不是像接受和赠送礼物那样先付出再收获的过程,而是说给予的同时就在获得。这既不是纯粹的自私也不是纯粹的无私,而是和谐统一的概念。
自由和尊严的概念经常被构架为以个人为中心。从共情的视角来看,这两个概念都可以放到关系中解读,而这种解读需要统一的看待自我与他人。
头图由“Shutterstock”提供。
原文来源:https://uxmag.com/articles/what-is-empathy(2014.11.04)
版权声明:该文章在UXRen公众号(cnUXRen)首发后方可转载,转载时请注明出处及译者、审校者信息,如有违背,UXRen社区保留侵权追责的权力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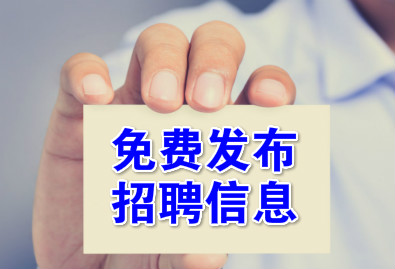






好文章!两位配合翻译真好!契合现代人需求,译者有思想!
与禅学相契合。